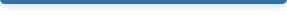喀什西北的台地上,恰克马克河静静流淌。河岸南侧有一片荒原,当地村民称作“汗诺依”——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意为“王庭”。这个颇具传奇意味的名字,早在19世纪末便出现在西方探险家的笔记中,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停留在传说与猜测之间。
2018—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大学及喀什地区文物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汗诺依遗址展开系统调查与发掘。随着无人机航拍、全站仪—RTK测绘、探地雷达与洛阳铲勘探、地层剖面的逐层揭露,一座由早期聚落演化而来的大型城邑遗址逐渐从历史的尘沙中显影。
作为汗诺依考古队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艾力江主持了这次考古发掘工作,他以专业视角记录遗址每一处细节的显露,也见证了一段被尘封的西域历史。
荒原不“荒”:
一座被时间覆盖的城市群
“第一次踏上汗诺依的土地时,脚下的台地和喀什周边许多荒原没什么两样,风带着沙粒掠过地表,只能看到零星的土埂和散落的石块。”艾力江回忆2018年首次进场的那一天时说。在他这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眼中,这样的地貌太过熟悉,但多年的西域考古经验告诉他,越是看似寻常的荒原,越可能藏着历史的真相。

艾力江(左一)向国家文物局验收专家组介绍考古发现。

汗诺依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玻璃
汗诺依遗址位于新疆喀什伯什克然木乡罕乌依村东北约3.5公里处,地处恰克马克河南岸台地,整体呈狭长分布,东西延展近5公里,南北宽2—4公里。“从地理环境来看,这里背靠台地、紧邻河流,是绿洲文明发展的理想区域。”艾力江指着遗址的航拍图说道。
2019年,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及其周边20余平方公里的区域展开系统探查与航拍。通过无人机的高空视角和地面的细致勘察,他们最终确认遗址范围内至少存在东西两座城邑,其中西城保存状况相对清晰,这里也成为后续发掘工作的核心区域。
考古人员所称的“西城”是遗址西北角的一方形城,也是文献中记载的“汗诺依古城”。2019年度汗诺依遗址发掘主要集中在西城,累计发掘面积达到1600平方米。“看着探方一点点向下推进,遗迹逐渐显露,那种心情很难用语言形容。”艾力江说。在他的记忆里,每一次遗迹的发现都伴随着队员们的兴奋与谨慎——清理出夯土城墙3段时,大家连夜记录墙体结构与夯筑痕迹;发现37座灰坑时,细致筛选坑内的每一件遗存;砖窑、房屋基址、道路的发现,让团队对城邑的功能布局有了初步认知。
随着高空正摄影像与精细测绘技术的应用,西城的城墙轮廓、城内地貌逐渐清晰。遗址上大量陶片沿台地呈弯月形密集分布,自城西南向东延展约1500米乃至更远,构成一条明显的人类活动带。对于这条绵延的陶片分布带,考古人员心中有了疑问:“这里是否存在过持续而有组织的城市生活?”艾力江和队友们开始将目光聚焦于遗址内的功能性遗存,试图从中寻找答案。
“列市”与作坊:
被陶片拼合的城市日常
西城以东约一里的探方19T11,成为解开疑问的关键区域。在这个仅100平方米的范围内,考古队在地表统计出2200余枚陶片,在地表下清理出28座灰坑。“灰坑里往往藏着当时人们生活的直接证据。”艾力江回忆,清理灰坑时,不断有惊喜出现:铜币、玛瑙珠、玉饰、金饰、铜饰、骨骼及尚未烧制的泥碗残件相继出土。“这些遗物的器类与材质十分多样,却又高度集中在这一区域,这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探方的性质。”
在梳理遗迹遗物分布规律、结合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后,艾力江和队友们有了初步判断:“这样的组合,很难解释为普通居住遗存,更有可能是居民区沿街开店的街市或手工作坊遗存。”他进一步解释,普通居住遗存的遗物多以生活用具为主,且分布相对分散,而这里不仅有大量陶片,还有贵金属饰件、货币等,更有未烧制完成的陶器残件,这些都指向商品交易或手工业生产的功能。
这一推断让艾力江立刻联想到文献中关于疏勒城“有列市”的记载。疏勒城是汉代西域唯一被记载为“有列市”的城市,而中原城市完成从里坊市场到街道市场的转变,是在唐代末期。“汗诺依西城南部和东部呈条带状分布的陶片区,恰恰可能对应这种沿街设市的空间形态。”
玻璃、水银瓶与窑火:
技术史线索
数量可观的玻璃残片与水银瓶碎片的发现,令艾力江格外兴奋。“这两类遗物的出现,是整个考古过程中最受关注的发现之一。”
2019年的调查中,艾力江和团队在遗址的不同区域共采集到玻璃残片百余枚。这些玻璃残片颜色丰富,涵盖浅绿色、黄色、蓝色、粉色及灰白相间等多种色彩,形态上则有管状、片状和环状等。通过初步的成分分析,判断这些玻璃可能包含吹制生产的钾钙硅酸盐玻璃。“吹制玻璃工艺在公元前后出现于西亚两河流域一带,在当时属于较为先进的技术。10世纪的喀什能够制作这类玻璃,说明当地的玻璃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艾力江解释道。
比玻璃残片更让艾力江关注的是多处地表发现的水银瓶碎片。“水银瓶并非日用品,它的用途相对特殊,有学者认为与玻璃生产直接相关。”艾力江介绍,亚欧大陆出土水银瓶的地区多为城市手工作坊区、商业仓储区或港口,中亚是水银瓶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学术界普遍认为其用来储存和运输汞(水银)与朱砂。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水银瓶在中亚和新疆的出现是在9—13世纪前后。
“它的集中出现意义重大。”艾力江分析,一方面,水银瓶的时代特征明确,且多见于地表,为判断遗址的时代下限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它与玻璃残片同时出现,印证了当时这里可能存在规模性的玻璃生产活动。
除了玻璃与水银瓶,一座独特的窑址的发现也让艾力江对汗诺依的手工业技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西城东北约30米处,考古队发掘出一座砖砌的方形地下窑址。根据窑室内残存的红砖及大量灰烬,艾力江和团队初步判断,这座窑址应是10—12世纪烧制红砖所用。窑北还有填埋炼渣炭灰的灰坑和操作坑,这说明当时的生产活动已经有了较为规范的流程。“这种砖窑形制在新疆考古中较为少见,而中亚类似窑址多见于11—13世纪。”艾力江说。
窑址的发现让艾力江更加坚定自己的判断:“汗诺依并非边缘聚落,而是嵌入区域技术网络之中的节点。这里的手工业技术与周边区域有着密切的交流与融合,这种技术的互动正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体现。”

汗诺依遗址出土的牙刷
时间的层叠:
一座城与多个时代
“汗诺依”这个称谓始见于一个多世纪前探险家的报告与日记中,却未见于明清时期的史料,因此难以断定该城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哪座城市相对应。艾力江坦言,关于汗诺依遗址的时代与性质,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这也是他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自斯坦因与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调查汗诺依遗址起,国内外学者就对其时代与性质提出了各种推断。考古学家黄文弼首次提出汗诺依西城可能是唐代疏勒镇的观点;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认为,汗诺依古城存在的时代为3—9世纪;《新疆古代城址》将古城时代推断为汉代到唐宋时期,《喀什地区文物志》则视其为宋元时期。
“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有相应的依据,但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之前缺乏系统的考古发掘和科学的测年数据。”艾力江说,这次联合考古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系统的发掘和科学的分析,厘清遗址的时代序列,为解决学术界的争议提供有力证据。
通过对地层剖面的细致分析,结合样品的测年数据,考古队最终确认汗诺依遗址存在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1—3层大体对应城墙使用的年代,城墙内部5处不同高度的包含物测年结果均显示为距今1000年,证实西城南墙的营建年代在10世纪;被叠压在城墙之下的第4—10层,地层时代早于城墙,有唐代、北朝和青铜时代中期地层,这反映了早在修建城墙之前,已经有人类长期在此活动。“这一发现说明,汗诺依遗址的起始与西城的营建年代存在一定的差距。”艾力江强调。
由于原始地貌不复存在,现今地表与古代地面可能完全不同。让考古队欣喜的是,城墙顶上的虚土与城墙上部墙体的测年结果相同,意味着城墙顶部的虚土是城墙长期腐蚀后粉化的结果。多处地表遗物测年显示距今约750年,“这说明西城与整个遗址大体在同一时期遭废弃,这为我们判断遗址的废弃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介绍道,结合遗址内出土的“开元通宝”“政和通宝”“大观通宝”等唐宋钱币,以及水银瓶、釉陶等遗物的时代特征,考古队最终推断:西城可能营建于10世纪,城墙局部可能经过修补与重建,最终在元代因河流变迁等原因而遭废弃。
疏勒、怯沙与喀什:
文献与遗址的对话
厘清了遗址的时代序列后,汗诺依遗址的性质问题成为艾力江和考古队员关注的焦点。“是否为汉晋疏勒城?是否为唐代疏勒镇?抑或仅是某一地方州治?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将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进行深入考证。”艾力江查阅大量历史文献,试图在文献与遗址之间搭建起桥梁。
“疏勒”之称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却不见于《史记》。《汉书·西域传》载:“疏勒国,王治疏勒城。”“我在研究中发现,不同语言文献中存在与‘疏勒’对应的词汇。”艾力江介绍,于阗语文献中有“Suli”一词,佉卢文文献中有“Sulig”,藏文《于阗史》中有“Shulik”,这些词汇被视为中文史料中“疏勒”的对音;《突厥语大词典》所载之“Suvla”,地名之方位与喀什噶尔一带相合;而在喀什市方圆百里之内,至今仍有多处名为“Suluk/Sulug”的地名。“这些都说明‘疏勒’这个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并且与喀什地区有着密切的关联。”
艾力江还发现,3世纪开始出现“疏勒”与“怯沙”等名称并存的现象,“怯沙”之称被认为是“khash”,发音正如今日的音译“喀什”。
《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达记》)中记载,“赤河来自疏勒西葛逻岭,至城西分流,合于城东北,入据史德界”,让艾力江对唐代疏勒镇的地望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贾耽著成书于公元805年之前,记载的‘疏勒镇’无疑就是8世纪的喀什噶尔城,反映了喀什噶尔河自西向东经喀什(市)流到巴楚‘唐王城’(即据史德城)自唐代到现代始终未变的情景。”艾力江解释道,唐宋的“赤水”、清代的“乌兰乌苏”、近现代“克孜勒苏”,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群用不同语言对喀什噶尔河的称呼。同一条河的三种历史名称,不仅反映出喀什具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唐代疏勒镇就是喀什噶尔城,不同语言的唐宋文献对该城的地望与河流描述有共同特征。
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更是记载了具体方位,有两条河流——克孜勒与吐曼——贯穿喀什噶尔城。“这一记载证实了唐宋疏勒城与喀什噶尔城实际上是同一座城市。”艾力江说。正如18世纪的《西域图志》所言,唐代的疏勒城就位于喀什噶尔城附近。
“史料显示,唐朝在疏勒地区实行军政并行的双重管理体系,出征中亚的重任主要由疏勒承担。”艾力江介绍,除了设置疏勒镇统辖军队之外,唐朝还设置疏勒都督府统辖其境内十五州,分别为疏勒、汉城、岐山、达满、遍城、半城、耀建、猪拔、演渡、双渠、黄渠、苦井、郢支满、乞乍和蒲顺。“所设州府的数量远多于龟兹和于阗,可见疏勒在西域军事防御体系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据点。”
汗诺依遗址与唐代疏勒镇到底是什么关系?艾力江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判断,“喀什市以东约25公里的汗诺依古城附近只有恰克马克河流经,吐曼河与克孜勒河与该城距离接近10公里,地理位置与《唐书·地理志》所载唐代疏勒镇地望特征不符,也不符合11世纪文献对喀喇汗都城地理位置的记载”。他进一步表示,通过系统调查,考古队确认汗诺依遗址西城(城墙)的时代为10世纪,初步排除了其为汉代疏勒城的可能。
“结合《新唐书·地理志》和《突厥语大词典》等文献记载,唐代疏勒镇的地望特征——三面环山、城在水中、赤河分流——与当今喀什市高度吻合。”艾力江认为,“从目前证据看,唐代疏勒镇应在今喀什市范围内。从汗诺依遗址的宏大规模、西城以东有明确的唐代地层的情况来看,尽管尚未发现唐代的城址,但遗址依然有可能是疏勒都督府所在,遗址中或有唐代文献中的‘汉城’存在”。
在荒野中坚守:
考古人的责任与初心
熟悉西域考古的人都知道,在新疆的荒原上开展考古工作,面临的困难超乎想象。艾力江却不愿过多渲染其中的艰辛。汗诺依考古队驻扎在条件艰苦的野外,夏季高温酷暑,最高气温达40℃以上,风沙频繁,常常一阵风过后,脸上、身上全是沙土;冬季则寒冷漫长,最低气温接近-20℃,给野外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身体上的疲惫是难免的,但每当有新的发现,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了。”艾力江笑着说。
虽然不愿强调自己负责人的角色,但作为项目的核心成员,艾力江始终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在野外发掘现场,我既要参与学术判断,对每一处遗迹、每一件遗物的发现进行专业分析,也要协调团队成员之间的工作,配合其他单位的同事开展测绘、取样等工作。”他说,考古工作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业,而是集体智慧与耐心的结晶。“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特长,大家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才能让考古工作顺利推进。”
在艾力江看来,考古工作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发现历史、解读历史,更在于保护好珍贵的文化遗产。“每一处遗址都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尽可能减少对遗址的扰动。”他介绍,在汗诺依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团队采用了精细化的发掘方法,对每一件遗物都进行编号、记录、拍照,确保考古信息的完整留存;同时,积极与当地文物部门、村委会沟通协调,做好遗址的保护与宣传工作,提高当地村民的文物保护意识。
“考古工作让我对‘责任’二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艾力江感慨道:“我们不仅要对学术负责,拿出科学、严谨的考古成果;也要对遗址负责,保护好每一处历史痕迹;更要对当地社会负责,让考古发现服务地方文化传承与发展。”
在时间深处:
读懂文明的多元一体
目前,汗诺依古城累计发掘面积已达4500平方米,城址、佛塔与手工业遗存的大体面貌逐渐清晰。在艾力江眼中,这座遗址所呈现的不只是某一段历史的痕迹,更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图景。
出土的遗物中既有具有本地特色的红褐色夹砂陶,也有受中亚文化影响的玻璃制品;既有中原王朝的钱币,也有西域风格的饰品。他解释道,西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的地方,汗诺依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展现了这种交融的具体过程。“不同人群在这里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支流。这种多元一体的特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也是我们理解西域历史的关键。”
“很多人问我,考古的意义是什么?对于我来说,考古就是为了理解真实发生过的生活,读懂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艾力江的声音平静而坚定,“每一件遗物、遗迹都是历史的见证,在时间深处沉默着,等待我们去解读”。而汗诺依这座在尘沙中沉睡了千年的遗址,正以它独特的方式,回应着这位考古学者的追问……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任冠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