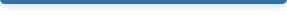柴怡赟(近代史研究所)
202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75周年。在整理所庆资料时,我再次打开为蔡美彪先生制作的专题片。当片尾那帧由蔡先生亲笔题写的七律缓缓展开时,笔墨间的赤诚与厚重,瞬间将我拉回与先生相处的岁月。那些藏在学术对话、日常陪伴里的珍贵片段,如潮水般漫过心头,在字里行间重读先生的学术人生,让我更懂何为“纯粹的治学者”。
“书成十卷鬓如丝,雪夜寒灯伴影时”,这句诗恰似蔡先生治学之路的缩影。先生与史学的缘分,早在青年时期便已扎根。1949年,他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研究院,专攻蒙元史,自此与内蒙古及蒙古学结下不解之缘。后来在专题片外景拍摄时,我曾随他重回法源寺——在那些字迹斑驳的元代石碑前,先生轻轻抚摸碑身,一字一句细数碑文中藏着的过往,眼神里满是对历史的热爱与敬畏。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对他而言,历史从不是故纸堆里的文字,而是鲜活的、值得用一生去追寻的“老友”。
我与蔡先生的交集始于2007年初春。彼时我刚入研究所不久,恰逢中国社会科学院筹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专题片,我有幸担任先生专题片的编导。初次拜访时,他没有丝毫架子,对《中国通史》编纂的幕后故事,以及范文澜先生对他的影响娓娓道来。那些看似平常的对话,让我逐渐将专题片的主题聚焦于“蔡美彪与《中国通史》的学术传承”。而他言谈间流露出的执着与严谨,更给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后辈上了关于“治学”的第一课:做学问,既要耐得住寂寞,更要经得起推敲。后来专题片的解说词与成片,先生都亲自审阅,直至完全满意,才同意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份对细节的较真,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2008年,因专题片的合作之谊,我有幸被选为蔡先生的学术助手,从此开启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学术陪伴之旅,直至先生晚年。那时先生已迈入耄耋之年,虽早已退休,研究所仍为他保留了工作室。每天他都会坚持从东总布胡同步行往返东厂胡同的工作室,40分钟的路程对年轻人而言尚且不轻松,他却风雨无阻,几未间断。每次我到办公室,总能看到他伏案工作的身影,桌上摊开的手稿、标注得密密麻麻的书籍,都在诉说着他对学术的热忱。
作为助手,我的工作大多是整理著述目录、誊录手稿、处理信函与外界联络。那时的蔡先生总把“抓紧写作”挂在嘴边。他常跟我说,要趁着头脑清楚,争取每年完成1—2部专著。80岁前后的几年里,蔡先生迎来创作高峰期,先后出版《中国通史》一至十二册合装本、《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辽金元史十五讲》《辽、金、西夏史》《学林旧事》《元代白话碑集录》《辽金元史考索》《中华史纲》《中国通史简本》《史林札记》《成吉思汗小传》等10余部专著。回想那段时光,尽管辛苦,却是蔡先生晚年生活中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因为身体健康,他每天坚持工作六七个小时,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学术研究工作中。这份对学术的纯粹热爱,无关名利,只关初心,深深感染着我。
先生不仅在治学上为我引路,更在为人处世上给我树立榜样。他著作等身,却始终淡泊名利。别人请他作序,他大多会婉拒,还常对我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挟名人以自重。”因此,他一生几乎不给人写序。生活上,他更是简朴到极致,极少主动申请课题经费或参与评奖。晚年多病时也从未主动要过奖金和补助,那些最终拿到的奖项,往往是出版社或研究所人事部门代为申请的。有一次,先生生病住院,按规定可申领补助,他却坚决不肯,说自己工资够用,留给有需要的人。最后还是时任人事处处长黄春生老师与我商量,瞒着他申领了补助再告知,他才勉强接受。还有一次,我见他衣服破了洞还在穿,实在不忍心,便按旧衣尺寸买了两件新的送过去。他很喜欢,却坚持把钱给我,说不能让我破费。这份清白做人、不占分毫的坚守,让我明白何为君子之风。
更让我感念的是,蔡先生对后辈的关怀从不吝啬。我虽身在科辅岗位,他却总鼓励我多看书、多积累,不要着急下笔;后来听说我到复旦大学读博士,他比我还开心,特意建议我去拜访历史地理学家姚大力教授。遗憾的是,那时的我因胆小自卑,最终没能鼓起勇气登门。
2016年11月是蔡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那天他在华侨大厦门口等出租车时突然晕倒,后脑磕伤。我接到通知赶到现场时,他已清醒,一个劲儿地说没事,就是脚一软摔倒了。此前他曾在科研大楼前摔过一次,但这次显然更严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身体虽有好转,却再也无法到研究所工作。从那以后,先生便开始在家办公,我隔段时间就会把订阅的报刊、书信送到他家;物业的李桂根夫妇帮忙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也会及时与我沟通他的身体状况,让我能随时处理突发情况。
新冠疫情来袭那段时间,蔡先生的听力和视力急剧下降,逐渐无法阅读和写作,每天只能靠看京剧消遣;一口假牙影响进食,导致他食量减少、睡眠变长。疫情后我第一时间赶去探望,大半年没见,曾经高大壮实的蔡先生瘦了许多,见到我时却开心得像个孩子,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我问他身体情况,他告诉我耳朵听不见了,电视也不想看了,我劝他买个好点的助听器,多在屋里走动,天气好就让老李夫妇推他下楼,还和他约定“要努力活到100岁”。可我知道,无法从事科研工作,让他的意志渐渐消沉,那份曾支撑他走过无数日夜的学术热情,似乎在一点点被病痛消磨。
2020年12月起,蔡先生的进食日渐减少,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冯时老师与我多次劝他去医院,他却坚决不同意。我们只能想各种办法:请社区医生上门就诊、购买浓缩营养液等,可即便如此,还是没能留住他。2021年1月14日凌晨,蔡先生驾鹤西去。他的外甥女发来蔡先生临走前一晚的照片,是刘小萌和韩志远两位老师去看望他时拍的,蔡先生离开病床,与两位老师坐在书房聊天,精神看起来不错。如今再看这张照片,才明白那是他在与陪伴了一生的书斋生涯作最后的诀别。
蔡美彪先生是我认识的人中活得最纯粹的人。他一生为学术而来,为学术而活,将所有的热忱与坚守都献给史学研究。如今蔡先生虽已远去,但他伏案工作的身影、温和的叮嘱、淡泊名利的品格,都已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前行路上的力量。每当重读他那首七律,“千秋青史情无限,百岁生涯憾有期”的字句便格外清晰,蔡先生用一生书写对史学的热爱,而这份热爱与精神,也终将在岁月中永远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