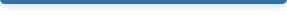◇桑逢康(文学所)
嘉陵江从广元的西边蜿蜒流过,10月底11月初正是秋季,江水特别清澈。江上修了东西走向的一座大桥,江边则是宽阔的沙滩,许多大小不一的木船停靠在岸边。因为水浅,广元一段不通轮船。
广元是四川北部的重镇,街面比较热闹,店铺很多,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地处南北分界线的秦岭以南,气候温暖,地里的庄稼和蔬菜绿油油的煞是可爱,与北方秋收以后直到来春,整个漫长的冬季一片光秃秃的荒凉景象迥然不同。抗战期间,我们母子第一次出远门路过这里,举目无亲,当地人更是一个也不认得。那时(1943年)父亲在永川英井中学教书,母亲和二哥四处打听去永川怎么走,不少人说有两条路线:一是从广元乘汽车先到成都,再从成都转车去永川;二是坐船从广元到重庆,再从重庆乘车去永川。前一条路线到永川时间上快些,但乘汽车花钱很多;后一条走水路要便宜不少,但船行比汽车慢,在路上花费的时间较长。母亲巴不得能够带着我们三个孩子早一天和分别六年之久的父亲团聚,但她知道身上带的盘缠已经所剩不多,两相比较之后当即决定坐船走。
于是,母亲带着我和二哥二姐来到了停靠木船的河滩。那段铺满沙子的河滩,不远处的大桥,自此便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参加工作以后,每逢出差或探望父母坐火车经过广元时,都会情不自禁、目不转睛地凝望那座嘉陵江上的大桥,江边的沙滩和停靠在那里的大小不一的木船。一边在心里想:“啊,当初我就是在这里上船的!”
从广元至重庆的水路,基本上是朝着东南方向下行,从川北大巴山系流向川中丘陵地带,途经许多县市和村镇。据说夏天洪水季节船借水势迅行如飞,冬天枯水季节船行缓慢,有的地方甚至会搁浅。深秋这个季节江流平缓,船行不快不慢,如果不是急着赶路,悠哉悠哉可以尽情欣赏两岸的风光:高高的山峰云雾缭绕,坡度平缓的丘陵上树木葱茏,竹林掩映处露出瓦房的屋顶或墙壁,还有一块块或大或小的绿油油的“坝子”(这是四川方言,把平地叫作“坝子”)。
那时我年纪小,尚未启蒙,只看见江水绿如蓝,不知道叫嘉陵江。“嘉陵江”这个名字是从同船的一个东北流亡学生嘴里听说的,他比我二哥还要大几岁,约莫二十出头,长得比较高大,穿一身学生装,竖领,上衣只有三个口袋,有别于“中山装”的翻领和四个口袋。我们乘坐的木船在山峰、丘陵和“坝子”之间穿行了一段之后,他旁若无人似的,站在船头上唱起了一支忧郁而又激昂的歌: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
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
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
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
……
我必须回去,
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
把我打胜仗的刀枪,
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我们母子也是从日军铁蹄下逃难出来的,所以对这个东北流亡学生抱有深深的好感。二哥二姐和我围着听他讲故事,于是又从他嘴里知道了“九一八”“少帅(张学良)”“东北抗日联军”。他告诉我们:他的老家在沈阳,在西北联大读了两年书,如今衣食无着,书是读不下去了,想到重庆谋个差事。
二哥问道:“差事不好找吧?”
“管他呢,试试再说。大不了我就在嘉陵江上流浪!”东北流亡学生忧郁地说。“我刚才唱的那支歌叫《嘉陵江上》,是作曲家贺绿汀根据端木蕻良的一首散文诗谱曲,端木蕻良也是东北人,算是我的老乡。”
二哥二姐由衷地发出了“啊啊!”的赞叹声。我虽然听不大懂他说的内容,但从心底深处对这个大哥哥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也很喜欢我,叫我“小弟弟”。
水流平缓,船行悠悠,像人在旷野中信步闲游似的。
船开了两三天,到了一个叫阆中的地方。东北流亡学生对大家说这是一座古城,三国时蜀汉大将张飞在此镇守,死后被追谥为“恒侯”,后人为纪念他建有“恒侯祠”,又叫张飞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尽人皆知,十多个乘船的人听东北流亡学生这么一讲,也都想上岸去看看,无奈船老大不同意。有一个川籍乘客用四川话嚷道:“天天坐你这个乌船,老子腿都坐麻了!上去走走,活动活动,又不多吃你一碗干饭,凭啥子不让去嘛?”
十多个乘船的人齐声附和,船老大只得同意靠岸,但又说船不能在这里干耗着。“你们上去看一看,我的船照常开,说好一个地方等你们。”
乘船的十多个人于是前呼后拥、嘻嘻哈哈上了岸,只有母亲留在船上照看行李。我跟着二哥二姐夹在人群中爬上了一个不高的山坡,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了古镇上的张飞庙前。东北流亡学生边走边向大家讲《三国演义》,讲刘关张孔明赵子龙……那个川籍乘客买了两瓶当地产的“保宁醋”,用四川话夸耀道:“你们晓得不晓得,这醋可是国宝,和茅台酒一起得过世界博览会的金奖!”
一个乘客质疑道:“保宁醋不是河北保定的吗?”
川籍乘客大声反驳:“名字虽一样,质量差得远,你买瓶阆中保宁醋尝尝就晓得了,河北保定哪比得了我们四川?”
船上的卫生条件极差,小孩子抵抗力弱,最容易招惹病灾。不知怎的,我的后脑勺上长了一个小疱,感觉到有点疼。母亲和二哥二姐也没在意,在山东老家时孩子头上长疱是常见的事。不料疱越长越大,越来越疼,我睡觉都不敢平躺着,不得不把头偏向一边去。母亲和二哥二姐这下有些慌了,但不知道怎么办,船上也没有医生,即使有医生我们也治不起。那位东北流亡学生走过来,对母亲说:“小弟弟的疱这样大,疼得他又哭又叫,不想办法怕是不行啊!”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想想法子。”
四川几乎到处都生长着茂盛的竹子。那个东北流亡学生上岸参观张飞庙时,在路上顺手折断了一小根竹子在手中把玩,他用随身带的削水果皮的小刀,把一截竹子削成一根竹扦子,尖的那一头细如针尖,又向船老大要了约莫二两当地产的烧酒。一切准备停当后,他吩咐母亲说:“大娘你把小弟弟抱紧了,我试一试……”
母亲紧紧抱住我,二哥二姐围在一旁观看。“大哥哥”又叫二哥拿一个小碗在旁边侍候着。他伸出一根手指头轻轻碰了碰我头上的疱,自言自语地判断:“里边都是血和脓,非挤出来不行!”我当时被母亲紧紧抱住动弹不得,疼得厉害但意识是清醒的,只是看不见在我的后脑勺上大哥哥怎样动作。二哥事后告诉我:东北流亡学生把那根削尖了的竹扦子用烧酒泡了泡,起消毒的作用,然后将最尖的那头一下子刺进我鼓鼓的大疱里,拔出又插进反复了几次,等于把它刺破了几个孔,又用手指挤压鼓疱,里面的血水夹着脓液一股脑儿流了出来。然后“大哥哥”又用烧酒在我的伤口上擦洗,疼得我哇哇大哭……
用现在的医学知识来说,这是最简单的外科手术,但在当时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却起到了绝佳的疗效:几天之后我后脑勺上的鼓疱就完全消失了,头也不疼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疤痕和后遗症。二哥称赞东北流亡学生说:“你还是神医啊!”
东北流亡学生笑呵呵地说道:“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比你大几岁,多念了几天书,多得了几场病,所以知道了一点点医学常识。”又鼓励二哥:“有条件最好多读几天书,最好是能上大学。”
嘉陵江在合川有涪江和渠江汇入,江面顿时宽阔了不少,水也深了许多,从合川至重庆可以开行轮船,小的轮船当地人叫它“汽筏子”。我们乘坐的木船是天黑以后抵达合川的,当晚就在那里过夜。已经治愈恢复了往日状态的我,看到有许多汽车在车前亮着两个大灯来来往往地开着,十分好奇,便随口嚷了一句:“汽车真多啊,比秦岭路上的多得多!”
东北流亡学生纠正我道:“小弟弟,那不是汽车,是汽筏子,也就是小火轮。你看……”
这时正好有两只开着大灯的汽筏子从挨得很近的水面上驶过去,灯光照得明亮的地方可以清晰地看见被汽筏子搅动的水波。由此我又长一个知识:江里河里不仅行驶木船,大江大河里行驶得更多的是轮船。那一夜合川的江面上小轮船、汽筏子川流不息,船前开着的大灯犹如天空上的一颗颗星星落在了夜色笼罩的江水里。小小年纪的我见景生情,突发奇想,就问东北流亡学生:“水里的星星捞得起来不?”
大哥哥笑着对我说:“你试试。”
“我不敢……”
合川离重庆很近了。嘉陵江、涪江和渠江汇合后水势加大,又是朝下游行船,所以过了一天就到了重庆的朝天门码头。我们坐木船自广元至重庆约有一个月。乘客们在朝天门码头下船后各自分手,包括那个东北流亡学生。他对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颇有些舍不得,一再说:“同乘一条船,胜读十年书。”又特别叮嘱道:“大娘,还有三个小弟妹,以后咱们一起打回老家去!一定的!”
二哥二姐齐声应道:“一定!一定!”我尤其舍不得为我治疱的大哥哥,但不知道说什么感谢的话才好,只好恋恋不舍地目送着他,在又高又陡弯弯曲曲的山城重庆,大哥哥拐了一个弯就不见了,但我心里永远记住了在嘉陵江上萍水相逢的这位东北流亡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