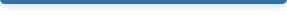当地时间4月16日,第四届中非文明对话大会在埃及伊斯梅利亚成功举行。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非洲研究院、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共同主办,主题为“古典智慧的现代价值——中非古代文明对当代全球性挑战的启示与镜鉴”。来自中国和非洲的知名专家、学者和外交使节参加会议,围绕“中非古典文明中的治理经验互鉴”“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城市与乡村治理:挑战与应对”“考古合作与文物保护”等议题展开深入对话交流。现将部分参会学者发言内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非洲研究院顾问 伊扎特·萨阿德·赛义德:
全球文明倡议为中非合作增添文化与人文维度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真实亲诚”的新时期中国对非政策理念,宣示中非是命运共同体,2024年又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202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为中非合作增添文化与人文维度,推动双方更深层次的互信与合作。通过中非文明对话大会等平台,双方强化文化与社会纽带,推动建立基于共同利益与相互理解的长期伙伴关系。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副校长 穆罕默德·萨阿德·扎赫卢尔:
搭建中埃人才培养与文化交流平台
中非文明对话大会在埃及举行,肯定了埃及作为东西方重要桥梁的国际地位,以及在促进不同文化和民族相互理解方面发挥的突出作用。苏伊士运河大学及其孔子学院作为实践典范,通过学术交流、职业培训及企业就业论坛等机制,搭建中埃人才培养与文化交流平台,并联动非洲其他孔子学院共享经验,破解协作壁垒,共同推进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今天我们齐聚一堂,既是为了回顾中非古老文明的辉煌,也是为了共同探寻古典智慧应对当代全球性挑战的启示。相信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与对话,必将为中非文明互鉴注入新的动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非智慧与中非力量!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古代史研究所所长 杨艳秋: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思想体系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所依据的思想是多元的。各种治理思想在所追求的治理方向、治理目标、治理方式上有着不同的表达,多种治理思想的融合与运用,形成了以“大一统”为政治目标,以“德治”为理想,以礼制、礼仪为规范,以教化、刑罚(礼、乐、刑、政)为手段,德、法并举,王道、霸道相兼,求变、求新的思想体系。
第一,“大一统”是治理思想的最高政治目标和国家治理的总体方向。“大一统”既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标识。统一而非分裂、融合而非隔绝,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造就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基调。第二,“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基础,同时也是人文主义在国家治理中的呈现和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底蕴最为深厚的基础思想之一。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强调的立君为民、民为国本与政在养民,就是从治理本体、治理关系、治理原则三个层面上表达了大一统社会下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和历史逻辑。民本思想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继承,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理念与政策措施。第三,“德治”始终是传统国家治理的主导思想。以德为主的统治模式以“民本”为核心,以“仁”“礼”为两翼,既彰显人文关怀,又申明和谐秩序,呈现出综合治理理念的特征。第四,治国先治吏的吏治思想是中国治理思想的重要特征。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古代历史上形成了吏以民为本、选贤任能、严以治吏等重要吏治思想。吏治思想所积累的治理经验和历史智慧,形成了包括考核、监察、奖惩等在内的吏治治理体系。第五,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源自对社会变动的体认,是中国传统治理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革新进步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改革变法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因时立事、承敝易变、居安思危一直是历代改革家推行新政的不竭动力与思想渊源。
以上五个方面的思想理念相互联系、互为一体,构成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体系,这是中华民族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所获得的宝贵治国之道。正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具有的这种体系性特征,得到历代王朝国家重视,并在继承中不断加以完善,使中华文明取得世所瞩目的长期性、连续性发展成就。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哈桑·拉加布:
中埃共鉴:“和而不同”理念的当代社会治理价值
“和而不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对埃及社会乃至全球治理具有深远启示。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理念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儒家思想强调统治者应广纳不同意见、吸收多元思想,从而推动国家长治久安。例如,中国历代王朝设立“言官制度”,鼓励直言不讳,以包容不同声音,实现社会和谐。在埃及,类似的理念早在古埃及文明时期便已存在。古埃及社会信奉的“玛阿特”(Ma’at)思想,强调真理、正义、平衡、和谐,是古埃及政治、社会乃至宇宙秩序的核心原则。法老被视为“玛阿特的守护者”,其职责不仅是制定法律,更要在多元文化、信仰和利益群体中维持社会平衡。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正面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共同挑战。中埃两国的传统治理智慧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启示,包括促进多元文化共存,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包容性发展; 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
对于中埃两国而言,“和而不同”不仅是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更是推动两国合作的重要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双方深化文明互鉴,推动互利共赢,增进民心相通,不断推进教育、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持“和而不同”智慧,进一步深化两国交流与合作,共同为构建更加包容、公正、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 唐晓阳:
“全球南方”崛起中的古典与现代——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案例的思索
“全球南方”崛起是当今世界形势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在现代化过程中,南方国家由于其古老多元的文化传统而呈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路径。西方最初推进现代化时强调颠覆古典传统,而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却与延续本国的古典传统紧密相连。以中国为例,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首要关键是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目标的统一。中国社会在选择现代化时从来不是像西方社会一般单纯追逐利益与效用本身,而是以国家独立富强、免受外侮为使命。中国的现代化没有与自身的历史传承相割裂,而是在前进路径上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在自主的目标指引下,通过自身的思考与选择决定了现代化转型方式,古典传统既是目标确定和路径选择的重要思想基础,又在行动与变化中体现了自己的生机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转型时,必须统一科技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目标,并通过在现代化语境下重新诠释古典文化而促进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实现自主而又生动灵活的发展。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王俊:
从非洲哲学到世界哲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持续加强,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斗争不断深入,以现代技术为标志的西方文明显露困境,“世界哲学”作为哲学研究的话题日益引人注目。当代哲学在大多数时候已不单单意味着“西方哲学”,而是多元图景的世界哲学地图。因此,今天我们普遍认可“哲学”内涵的扩充,即除了古希腊—欧洲哲学之外,东亚、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有其独特的哲学类型。
非洲哲学是世界哲学地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也不应该停留在孤立的区域文化和人类学研究层面,而是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以非洲与世界的互动对话以及多维度的比较研究为线索,考察非洲哲学、思想和文化的内涵及意义。对非洲哲学的研究对于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世界哲学图景有着丰富的构建性意义,比如非洲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方式给西方以及当代主流的政治观念和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诸如口述哲学等非洲哲学的特有方式更激发了我们对于哲学概念本身的反思,促进了哲学内涵的丰富和扩大。
城市和乡村都涉及人的共同体问题。在这个领域,非洲和中国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有“乌班图”(Ubuntu)的概念,既指人性、仁爱,也包含了“生存、团结、同情、尊重及尊严”等价值。乌班图哲学将道德诠释为对他者的责任,进而拒斥个人主义,强调建立睦邻友爱与注重责任的社群关系。乌班图精神倡导以宽容及仁慈的态度对待异己者或他乡人,充分展现了非洲人对陌生人的尊重及接纳,勾勒了建立世界范围内人人互助的共同体愿景。乌班图哲学不仅强调人因与他者和集体的关系得以成为自我,同样关注主体间互联与合作,强调人与他者、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观念。类似的观念在中国儒家哲学的“仁”“天下为公”“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等思想中也有充分体现。非洲和中国的这些传统思想,为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建构理想的城市和乡村生活奠定了观念基础。
今天,我们要以整体性的视野,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启一个容纳不同文化传统及多元哲思的公共空间,突出不同文明传统之间整体和局部的关联,弘扬人道主义、宽容、多元等重叠共识和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安春英:
中非农业文明的历史定位、价值意蕴与现实合作
中国和非洲都是世界农业发源地,双方各自创造了具有独特价值的农业文明,是世界农业文明宝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非农业合作走过60余年发展历程,双方农业合作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而且具有强劲的现实动力。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发展合作的引领者,非洲作为“全球南方”的关键成员,深化中非合作,将有力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发展进程,以农业合作为切入点可务实推进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
当下,中非农业合作一方面需深化传统领域合作,如援建基础设施、派遣农业技术专家、创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投资农业产业园、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特别计划”框架下的“南南合作”等;另一方面,需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增强农业发展内生能力。具体而言,即依托相关机构举办农业培训班,通过经验分享以及实地考察等活动,增加学员对于农业发展与综合治理的感性和理性认识,由此为非洲国家农业发展提供“他山之石”。需要指出的是,中非农业合作经验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并不仅仅是中国向非洲传播农业技术。事实上,非洲国家农业发展了多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技术。例如,津巴布韦当地农民在发展种植业时,采用玉米、高粱和小米混合种植的方式,再补种其他本土耐旱作物,对于保持土壤水分、提高土壤肥力、防治病虫害方面具有独特作用。上述农业发展经验值得中方学习借鉴。
展望未来,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中非农业合作将以在地化合作丰富农业发展知识产品的共享机制,出现越来越多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与此同时,中非合作将聚焦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产业发展领域的应用,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进自动驾驶无人机从事农田测绘、水稻播种、农药喷洒等作业。可以期待,中非农业合作内容将不断创新,进入3.0版合作阶段。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查尔斯·奥努奈居:
传统与现代:中非治理经验的交流与互鉴
尽管中国与非洲之间地理距离遥远,但双方早已开始良性互动,开启了彼此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篇章。很早以前,埃及人就通过陆路和海路到达中国。7—15世纪,双方工商业往来迎来了繁荣时期,中国秉持开放态度,积极推动对外贸易与海外交流。中国水手勇敢探索海上航线,穿越印度洋,抵达非洲东海岸。明朝官员郑和七下西洋,推动古代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实现巨大飞跃。这一壮举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对非洲的认知,他们据此绘制出三角形的非洲地图,比欧洲人绘制类似形状的非洲地图早了一个多世纪。尽管中非交往曾因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被迫中断,但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及一些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独立,双方开启了交流与合作的新纪元。
当前,中非已开启共筑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双方合作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金砖国家等重要机制蓬勃发展。为激发合作活力、拓宽合作视野、深化相互了解,大力推进交流互鉴已成为中非合作的关键议题与核心行动。其中,中非治理经验交流占据着重要地位。
(练志闲/译)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主任 刘源:
商代文字中的动物形象与中国思维特点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又是思维的工具,文字的构造、语言的使用中往往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汉字自殷商时代发展成熟,到今天仍被广泛使用,其蕴含的古老观念与传统思维也流传至今。
汉字保存了古人观察与表达自然的方式,反映中国文化的思维与视角,汉字中的动物形象就是典型例证。例如,商代文字“鸟”“隹”均指鸟类,但“鸟”强调鸟类站立、收拢翅膀的姿态,“隹”则强调展翅姿态。商周汉语中,“隹”多读作“唯”,表强调之义,如殷墟甲骨卜辞常见“唯某人令”。这种以“唯”字带出宾语前置的思维习惯一直延续至当代汉语,如唯才是举、唯命是从、唯我独尊、唯利是图等。这反映了语言文字对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充分说明古文字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是中华民族集体意识的重要根脉所在。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所长 彼得·卡格万加:
中国和非洲携手共进、走得更远
1903年,著名的泛非主义者W. E. B·杜波依斯指出:“20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限的问题。”在那个时代,非洲和中国都遭受着外部势力的占领与剥削,非洲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都曾因此而中断。作为外交政策和西方全球霸权的武器,西方现代化模式巩固了西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上的统治,加剧了非西方地区的贫困与欠发达状况。
经历不断探索,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表明,贫困并非任何文明的诅咒!它激励着非洲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和工业化道路。在21世纪伊始,非洲踏上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征程,以实现自身的发展愿望。非洲知识分子和领导人推广“非洲复兴”理念,“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成为了非洲大陆去殖民化的响亮口号,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以及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更是勾勒了非洲大陆的未来发展蓝图。
非洲谚语说:“想要走得快,就一个人走,想要走得远,就一起走。”在 21 世纪,中国和非洲决定携手共进,走得更远。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得到了非洲全力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中非合作的“双引擎”。与此同时,中非人文交流领域不断拓展。截至目前,中国已在非洲合作设立了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它们广泛分布于非洲大陆的众多高校中,促进着两大古老文明的互学互鉴、理解交流。
当今世界正处于过渡时期的困境之中,旧的秩序正在消亡,新的秩序尚未诞生,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无处不在。非洲和中国肩负着推动文明对话、实现共同发展、激励各方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的历史使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必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崇高愿景下的多极世界格局让路。
(刘雨微/译)